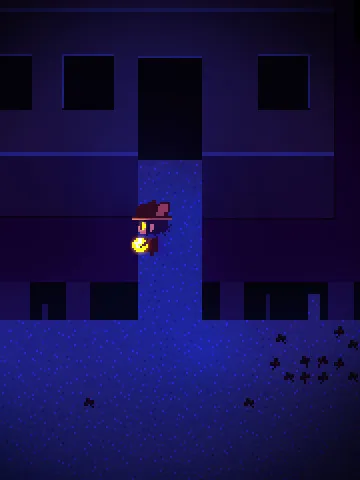(2017 年 2 月 8 日)
“我只是想站起来……我真的……
我脑子里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我只是......”
— 罗伯特·德尼罗在《出租车司机》中饰演特拉维斯(《出租车司机》于 1976 年 2 月 8 日上映)
“我拿出剃须刀,
我做了上帝不允许我做的事。
警察正在追捕我。
但至少我证明了我是一个男人。”
— 雷蒙斯 (The Ramones) 的《53rd & 3rd》(1976 年 4 月 23 日发行)
“出租车司机”
在美国上映40多年后,《出租车司机》如今似乎已成为美国乃至西方文化的一个关键符号:它准确地预言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享乐主义和异化的孤独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牛仔等美国文化正面形象的阴暗面,而这些形象也摇身一变成了恐怖分子。
在早期电影中,例如《肮脏的哈里》(1971 年)和《龙》(1974 年),复仇者通常来自社会内部——从婚姻到警察工作。他们必须失去一些东西,即使只是一枚警徽。
肮脏的哈利(肮脏的掠夺
相比之下,《出租车司机》中的特拉维斯·比克尔则完全被孤立了,甚至可以说是被诅咒了:“我一生都是孤独的,在酒吧、车里、人行道上、商店里,到处都是,无处可逃,我是被上帝抛弃的孤独者。”他对颓废的纽约的抨击——约翰·保罗·施拉德在剧本中完美呈现了这一点,但紧接着的是一个同样颓废和凄凉的替代方案——是由他最亲密的朋友、另一位司机、“巫师”(彼得·博伊尔饰)讲述的:“我羡慕你,你的青春。你可以出去泡妞、喝得酩酊大醉,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无论如何,你别无选择,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完蛋了。”
特拉维斯独自住在一间昏暗的公寓里,极度渴望与周围的环境产生联系。但在他的眼里,女人要么是处女女神,要么是妓女。影片中最让人心痛的场景之一,他带着香艳的贝茜(赛比尔·谢泼德饰)去电影院,但屏幕上放映的电影确实是成人电影,这自然引起了贝茜的厌恶,但特拉维斯却毫不知情。
在把他的女神当成妓女对待后,他试图拯救一个真正的妓女——艾瑞斯(朱迪·福斯特饰),结果却很糟糕。即便如此,他的幻想也破灭了:肮脏的哈利式冷酷人物开始了一场混乱而漫长的枪战——一场肮脏的血腥屠杀。
到 1976 年底,《出租车司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 130 万美元的预算获得了 2100 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场狂热的梦境,纽约市是其中最大的明星:一个闪闪发光、闪烁着霓虹灯的噩梦。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推搡着,大喊大叫,兜售东西,还有皮条客。广告牌和明亮的招牌暗示着连环杀手和变态的性行为,在电影中,纽约是一个混乱的欲望迷宫,它承诺一切,却什么也没给。
所有危险的按钮都被按下了:混乱、谋杀、性作为消费主义的终极表现。整个事情正在失控。
特拉维斯将自己视为三岛由纪夫式的人物,决心洗清自己的罪孽——不仅是来自社会,也来自他自己的内心。但他却深陷这种堕落:吸毒、吃垃圾食品、夜里以极快的速度行走。他的生活一团糟,甚至最后的枪战也被他搞砸了:他最终杀死的不是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帕兰坦(原剧本中的情节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刺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的亚瑟·布雷默的故事),而是三个不起眼的黑帮、骗子和皮条客。
《出租车司机》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从始至终都近乎完美。贯穿整部电影的虚无主义(“我们都完蛋了”)的产生过程很有意思:特拉维斯留着一头引人注目的长发,戴着方形太阳镜,穿着一身朋克风格的服装,让人想起了朋克时代。
特拉维斯像布雷默以及跟踪他的杀手们一样,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这一事实赋予了影片强烈的事实性而非意识形态支撑:特拉维斯最后的爆发不是随机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这在影片的逻辑下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纽约以外城市的社会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当《出租车司机》忙于电影准备、剪辑和制作并最终定于 1975-1976 年上映时,雷蒙斯乐队正忙于录制专辑:1975 年发行了两盘试听带,1976 年 2 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雷蒙斯》,其中包含 14 首曲目,与《出租车司机》几乎同时发行。
专辑封面是一张 Roberta Bailey 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乐队靠在纽约鲍厄里区一堵满是涂鸦的墙上,看起来像罪犯和骗子。这张专辑充满了乐队对纽约的感性,在关键歌曲“53rd & 3rd”中得到了明确体现——这首歌讲述了性羞耻和内疚导致谋杀幻想。
雷蒙斯乐队专辑封面
当雷蒙斯 (Ramones) 忙于录音和拍摄《出租车司机》时,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西贡于 1975 年 4 月沦陷,越南战争结束(特拉维斯和 53rd & 3 都是越战老兵,这绝非巧合);查尔斯·曼森 (Charles Manson) 的追随者、曼森家族的丽奈特·弗洛姆 (Lynette Fromm) 和莎拉·简·摩尔 (Sarah Jane Moore) 于 1975 年 9 月企图暗杀福特总统;福特总统发表演讲,拒绝让联邦援助使纽约破产,《每日邮报》以“福特正在摧毁这座城市”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
和后来形成了自己独特审美的其他几个城市一样——克利夫兰、伦敦、巴黎——当时纽约是一座被遗忘的小镇。1975 年末,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玛丽·哈伦住在纽约曼哈顿第 14 街:
“我记得站在窗边,望着下东区,感觉整个城市都在腐蚀和崩塌,但感觉很棒。空气中弥漫着虚无主义和死亡的欲望。这听起来有点傲慢,但当时住在纽约的感觉之一就是渴望被遗忘,就像这座城市一样,你正在崩塌和瓦解。然而这是一件神秘而美丽的事情。”
1975 年末,她为《朋克》杂志第一期采访了雷蒙斯乐队:“我不知道他们是好是坏,我是否喜欢他们,我只知道雷蒙斯乐队非常出色,我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乐队。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歌词中写道‘用棒球棒打那个人’——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就像一支名为 King Crimson 的伦敦摇滚乐队写的东西。这很有趣,但也非常真实,他们想做一些真实的事情,即使这是非法的事情。他们似乎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
和《出租车司机》一样,雷蒙斯乐队与嬉皮士虔诚毫无关系: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专辑的歌词结合了极端主义的缩写词——CIA、SLA——和恐怖的引用(德州杀人狂)、极权主义的形象(“我是一名昏迷中的士兵”)和深深的厌恶(“这难道不让你恶心吗?”)。
《出租车司机》和雷蒙斯乐队都表达了对自由主义和商业化的嬉皮士文化的右翼批判观点:拒绝轻松、过于商业化的社会,这种社会暴露了一切——可卡因、麂皮、水床。这导致了一种颓废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在性和社会上堕落,而且——更糟的是——艺术家的自我放纵。
《出租车司机》与雷蒙斯合唱团有着密切的联系:裸露的躯体、充满敌意和对抗的内容、刻意制造的惊悚感。即便如此,《出租车司机》也做出了足够多的妥协——尤其是暗示性、救赎性的结局——尽管在细心的观众看来,结局并没有解决问题:《出租车司机》在 1976 年 2 月连续三周荣登美国票房榜首,随后在 3 月下旬和 4 月初连续两周荣登榜首。
相比之下,雷蒙斯乐队在排行榜上的最高排名仅为 111 位,直到 2014 年才跃居第一,但它对英国朋克音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自 1976 年发布以来加速了该音乐流派的发展。
《出租车司机》于 1976 年 9 月在英国发行,同月,性手枪乐队彻底改变了英国朋克文化,另一种对抗性美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艰难条件。可以说,《出租车司机》和雷蒙斯乐队这两件诞生于纽约的艺术作品,现在看来具有非凡的先见之明:如果雷蒙斯乐队改变了摇滚乐的质感,那么《出租车司机》预示了出租车连环杀手大卫·伯科维茨的出现,他是萨姆的儿子,于 1976 年 7 月犯下了第一起谋杀案。1977 年 5 月,他给《纽约邮报》写了一封信,读起来就像是特拉维斯叙述的复述:“纽约的阴沟里到处都是狗屎、呕吐物、劣质酒、尿液和鲜血。”
《出租车司机》和雷蒙斯乐队也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即将席卷西部的右翼政治。正如玛丽·哈伦 (Mary Harron) 评价纽约朋克时所说:“人们需要谈论一些负面的东西,因为它具有解放性。它是如此坚硬、冷酷、光鲜,代表着某种事物的终结。它是一种寻求和毁灭的美学。”
雷蒙斯乐队本身持有多种政治立场——歌手乔伊·雷蒙是左派,而吉他手约翰尼·雷蒙则是狂热的共和党人——但他们坚持说出令人不快的事实,这导致他们采取极端立场,而为了获得主流认可,这些立场很快就软化了。
如果说雷蒙斯乐队加速了朋克文化第一波的兴起,那么《出租车司机》则定义了 1979 年以来席卷英国和美国的朋克文化。特拉维斯的没落从他的头发上可以看出来:起初,他留着朴素的短发。然后,他把头发剃得乱七八糟。最后,在他疯狂杀戮的过程中,他留起了浓密的莫霍克发型。
这张照片背后美国军方与印第安人的联系显然是有意为之:这是一种仪式性的、战争般的发型,旨在纪念阵亡士兵和被遗弃的人。1976 年,朋克文化尚未在美国兴起,在帕拉坦集会的人群和口号的映衬下,特拉维斯的莫霍克发型显得非常奇怪和显眼。他看起来像个疯子。
《出租车司机》没有雷蒙斯专辑中那种俏皮的黑色幽默,而是粗犷而残酷,能够发挥自己的能量。这是特拉维斯第一次出现在主流文化意识中。后来,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的凶手蒂莫西·麦克维、那些大学炸弹袭击者以及一系列校园枪击案的凶手似乎都是特拉维斯的替身。
特拉维斯提醒我们,极度的疏离和孤独会如何演变成无法理解的愤怒:“听着,你们这群混蛋,这家伙再也受不了了。他要站起来反抗那些卑鄙小人、变态、傀儡、卑鄙小人、垃圾。这家伙要站起来,这家伙……你死定了。”
合作邮箱: